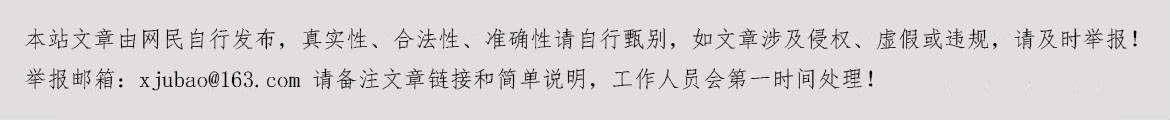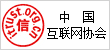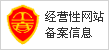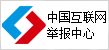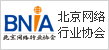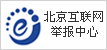淮阳便民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商旅生涯、综艺娱乐、生活百科、房产家居、国际资讯、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美国中期选举,保守派已锁定胜局?
2022-11-12 12:04:51
编者按
据澎湃新闻报道,美国11月8日的中期选举结果即将揭晓。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在选前最后一个周六(11月5日)均前往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为其所属党派的参议院候选人站台助选。 当前,美国经济濒临衰退,党派恶斗不止,“金钱政治”与政治暴力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在种族、堕胎权、枪支、犯罪、气候等一系列问题上严重对立,美国媒体纷纷用“混乱的选举”“民主岌岌可危”来描述这次中期选举。为争夺两院控制权,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均投入巨大赌注。据统计,今年的竞选总花费预计超过167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中期选举。拜登在宾州指出, “这个结果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我们的国家……这是一个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愿景之间的选择。”而在当地时间11月7日,推特新任“掌门人”马斯克在推特发文,建议独立选民在本届中期选举中投票支持共和党。马斯克的亲自下场“拉票”,赢得了不少右翼保守人士的青睐,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成员已经预测,共和党会在中期选举中大胜。
美国中期选举出现的此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全面升温?对此,理解冷战后美国的政治保守化运动及其根源,对理解当前美国的政治局势具有启示意义。本文指出 ,美国所谓的政治极化只是一种错觉,是在理解美国时仅局限于美国政治小棋局表象而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如果将美国政治趋势放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棋局中理解,就会发现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走向保守化,而非走向极化。本公众号特推出本文,供读者思考。
极化还是保守化
——冷战后美国政治保守化运动及其根源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史艳|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博士后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问题的提出:极化还是保守化
当下,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如火如荼,这主要源于美国府会斗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以党划线”的投票倾向以及美国各类选举中两党日趋白热化的政治较量,相关研究者提出了“政治极化”“否决政治”等命题。事实上,此种政治极化的观点基本上是将上述乱象放在美国政治坐标系中来测量的产物。如果把美国政治乱象放到世界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就会发现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保守而非越来越极化的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利益政治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一条主线。从利益政治的角度观察,所有的政治争论均可以左、中、右来划分。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争论一度成为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格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作组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世界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以美苏冷战对峙为基本格局主导了二战后的政治走向。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出现大变局,在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左翼思潮出现老左翼思潮和新左翼思潮的分化。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思潮陷入低潮,“文化左翼”在西方日益举起了左翼思潮的旗帜。冷战结束后,美西方曾一度沉浸在“冷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思潮不胫而走,甚至有人乐观地宣布“历史的终结”,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和《新自由主义》成为其旗帜。相比之下,保守主义并没有随冷战结束而刀枪入库,而是在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越来越滑入右翼保守的轨道,催生了以反建制主义为代表的“另类右翼”的崛起。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新政”的冲击下,美国族群冲突、宗教摩擦和阶级分化交织叠加、相互激荡,直接刺激了右翼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导致右翼保守主义鱼贯而出,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尖锐挑战。
进入21世纪后,以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和在欧美发达国家形形色色的反建制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为标志,右翼保守派不仅在英美两党制国家通过抛弃其基本价值观掌权,而且形形色色的右翼反建制主义在欧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上升,其涵盖了宗教右翼保守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等众多政治思潮。环顾世界,日新月异的新全球化浪潮和日益深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美国国内社会,形形色色的“失利者”逐步汇聚在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旗帜下,不断侵蚀着民主主义和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些所谓“另类右翼”的崛起不是保守主义的进化,而是对保守主义的批判,以“人民的名义”强调划分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分界线,不断释放着反精英、反建制的社会文化思潮。不难看出,右翼保守主义在21世纪发达国家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客观趋势,当前美国政治发展趋势的主流是保守化,而不是极化。
马斯克推特
美国保守主义及其发展线索
保守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基本立场来看,保守主义认为人性恶、无理智、缺乏责任心,而且欲壑难填,在政治上更看重传统、经验、权威、等级和秩序。在面对社会变革方面,保守主义倾向于向后看,强调精神生活具有永恒的价值,更看重老人的经验而非年轻人的想法,本质上是一种老人的哲学,推崇过去的时尚、道德观念和体制制度,轻视物质进步。正因如此,保守主义是一种偏重安于现状的政治思潮,更多代表着中上层社会力量的利益。当然,由于传统和现存秩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有极不相同的含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保守主义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存在着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另类保守主义的区别。
(一)保守主义:关注上下之争,核心是权力与权利之争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面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大变局,保守主义采取了维护旧秩序的保守态度,主要代表世俗君主、土地贵族和封建上层阶级的利益和立场,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传统,其基本主张是反对社会重大变革,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爱尔兰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圣公会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等。面对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保守主义极其重视现存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些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此相适应,保守主义反对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认为传统和秩序压倒一切,所谓的理性和激进革命最终会造成巨大的祸患。显然,面对来自中下层阶级的崛起,保守主义站在上层权贵阶层的立场,否认、抗拒和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反对激进意识形态革命,不愿让中下层获取和扩大政治权利,主要关注焦点是上下之争,核心是权力与权利的争论,不承认中下层阶级具有参与治国理政的正当性。
美国是保守主义思潮的后来者。20世纪中叶之前,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英国。直到二战结束,美国都没有形成系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其保守主义是二战后以挑战居于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登上美国历史舞台的。尤其是面对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举起了保守主义的旗帜,以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古典自由”重新定义了保守的内涵。另外,一批注重在文化领域中展示保守主义价值的思想家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等则挖掘政治的“宗教和道德内涵”。此外,还有一些长期与苏联打冷战的斗士也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严格来讲,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美式保守主义与英国保守主义大异其趣,其不仅在思想成熟度上与英国存在天壤之别,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鱼龙混杂、貌合神离。直到1955年,在小威廉·弗兰克·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创办《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后,美国式保守主义才算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平台和思想阵地。即便如此,这一脆弱的美式保守主义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内部分歧,难以与体系完整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相媲美。
(二)新保守主义:关注左右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
先天发育不良的美式保守主义在美国步履蹒跚。1980年代前,其既没有在政治和思想精英中获得一言九鼎的“泰山北斗”地位,也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政治号召力和政策影响力都十分有限。然而,二战后风靡一时的民权运动和文化左翼的出走,加上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乱局的发展,刺激了美国思想界和社会各界的神经,整个舆论弥漫着对自由主义之“价值相对主义”的失望,驱动着基于保守价值的思想合流。一批从自由主义阵营中出走的“认清现实的自由派”和形形色色的保守派交织激荡,刺激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挑战者的“新保守主义”崛起,形成了财政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经济保守主义以及宗教保守主义的“多声部大合唱”,尤其是街头保守派和书斋里的保守派共同找到了代表自己政治旗帜的总盟主——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总统,也找到了高举保守主义旗帜的思想巨擘——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自此之后,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到处都有新保守主义的阵地。从里根到老布什,再到小布什,新保守主义的政策路线一脉相承。尽管内部不乏争论,但在美国一直呈现出理直气壮、舍我其谁的霸气,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的影响日益增强。
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潮,其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新保守主义思想先驱为1950—1970年代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这一政治哲学流派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反对自19世纪以来的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思潮,他们批评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将思想界搞得一团糟,反对自由派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坚持形而上学的“价值普遍主义”立场。他们越过启蒙一代的思想家,直接回归“希腊精神”和“罗马美德”,坚持古典的“德行”概念,以自言自语的方式,将自然权利、私有制、人权、民主政治和法治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理想政治制度,甚至认为这一切得到了上帝的恩准加持,而无视人类历史其他文明形态的特殊性,鼓吹美国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正宗衣钵传人,是人类文明的真正灯塔,认为除新保守主义价值观外的其他一切都是异端邪说。不难看出,新保守主义的关注核心是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左右之争,核心还是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同判断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其理想中最好的制度模式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除此之外都是不正当的。
(三)另类保守主义:关注内外之争,核心是认同之争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保守化倾向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加速发展,“另类右翼”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的急先锋。就内部因素而言,美国社会日益为一些后物质主义的话题所困扰,比如堕胎问题、LGBTQ问题、艾滋病问题、宗教权利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胚胎干细胞问题和枪支控制问题等。无论是新左翼还是新右翼,其所关注的问题均是一些后物质主义话题,政治的分界线从传统的利益政治转向了认同政治,以及基于认同政治所引发的道德冲突和“文化战争”,进而激发了民粹主义(Populism)在美国社会的大爆发。就外部因素来说,“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的反恐战争,引发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紧张。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反美主义情绪更成为多数保守主义者形成共识的黏合剂,退群、废约、筑墙、断链以及内顾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思潮不胫而走。那个曾经高举全球化旗帜在世界舞台上高歌猛进的美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损人不利己、以邻为壑的美国,这一切都构成了美国保守派中“另类右翼”崛起的政局。
事实上,所谓“另类右翼”,最初不过是一些“白人至上论”者和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用来界定自身及其意识形态的标签,它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粉丝群的疯狂追捧,日益成为互联网积极分子和观点极端保守、反对社会变革、反全球化、反建制且拒绝接受主流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极右翼个人和松散团体的总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背后的一个强大支持者——QAnon运动,这个运动最初由鼓吹“白人至上论”的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Bertrand Spencer)发起,后在特朗普竞选中发展成为一个“另类右翼”的激进团体。从政治立场来看,“另类右翼”激烈反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奋力抵制“政治正确”,坚定反对各种各样的建制派政治思想和具体政策主张,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认同政治,争论的分界线是内外之别,即表现为团体内认同与团体外不认同的反建制立场,也表现为国内认同与国外不认同的反移民和反全球的排外立场。
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根源
为什么美国日益走向政治保守化?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着现代社会转型引发政策立场分化的国内根源,也存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引发优势易位效应的国际根源。主流学界认为,美国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国家,缺少封建贵族集团,也缺乏无产阶级的土壤,美国国内政治的争论不过是不同自由主义的流派争论而已。美国之所以从一个以自由民主立国的国家日益走向一个保守主义的国家,根本原因是美国自身变化与美国和世界关系变化的综合作用。其中,前者为保守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后者则为保守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外部条件。
(一)美国自身的变化
显然,美国是一个移民垦殖社会,缺乏英国保守主义产生的环境条件,这导致美国保守主义先天发育不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美国保守主义的成长最初源于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且此种反思主要存在于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其中,前者表现为自由主义越高涨,则保守主义的价值观越坚定;后者表现为经济领域中的转型越深入,则社会领域中的保守主义基础越深厚。尤其是在美国分权制衡体制和两党政治框架内,此种现象很容易给人们造成美国政治日益极化的错觉,从而掩盖了美国政治日益保守化的本质。
文化保守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战后,伴随着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自由主义潮流中的理性主义、政治正确等原则开始受到一些思想家的质疑。以丹尼尔·贝尔、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主义和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轴心原则过于强调以个人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这造成了近代以来的很多社会灾难。为此,奥克肖特提出了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保守主义,与其传统的联系(如宗教、历史主义、道德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等级)相脱离。贝尔则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要求清算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以来的启蒙主义,回到古希腊罗马精神,重估价值。此种早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直接驱动了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的蔓延,进而成为“新左派”与“新右派”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论争。随着自由主义倡导的多元主义(Pluralism)和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盛行,冷战后的主流保守派节节败退,很多思想主张被“新左翼”所吸纳,整个世界呈现出“超越左与右”的新态势,令“另类右翼”非常不满。尤其是美国人口结构中白人的相对比重下降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我们是谁”的担忧,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到《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集中地揭示出了白人比重下降所引发的美国认同政治危机。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另类右翼”的核心思想就是强化白人认同,摈弃建制派保守主义,把白人种族-民族主义作为其基本价值观。尤其是主流保守派在堕胎、同性婚姻和大麻合法化等文化价值观和移民问题上节节败退,也为“另类右翼”的崛起提供了温床。哈佛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主持了一个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涵盖了约100个国家和地区90%的人口,发现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物质价值到诸如归属感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文化迁移,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活质量,关心人生价值,在超越物质丰裕的层面思考政策的超物质价值意义。尤其是Z世代的崛起推动人们积极参与新身份集团,支持堕胎自由的群体、同性恋群体和女性主义群体等边缘群体崛起,社会裂痕更多地表现为基于身份政治而产生的道德冲突。近年来,堕胎问题、同性婚姻问题、宗教权利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胚胎干细胞问题、艾滋病防治问题以及枪支控制问题等,其本质都是新身份群体不认同既有意识形态的产物。
财政和经济保守主义也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20世纪以来,面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垄断、不公平竞争、环境污染和政府腐败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重建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从罗斯福新政到“伟大社会”,美国越来越面对一个效率低下的“大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理论兴起,要求减少国家干预,放松行政管制,制止行政专制以及扩大公民自由。它们以“经济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上的保守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主义”为纲领,反对大政府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发表政治动员的“95条论纲”,进行基层动员工作,就其保守政治议题游说国会,插手选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同时,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转型,美国经济也日益向着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形态转型,美国保守主义在数字化转型的刺激下日益壮大,驱动着美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众多思想将辩论战场从学术殿堂转移到互联网。此种带有强烈情绪化特征和从众效应的近身肉搏式辩论,更有利于自白式的普遍主义,而不利于理性辩论基础上的思想对话。即便是很多关于专业经济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流于尼采化的普遍主义,而非洛克式的理性主义。新保守主义就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政治思潮,它一方面主张阐释文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重构古典精神,试图推翻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路线,重构“西方传统”的新路标;另一方面,它直接承袭了尼采主义的独白式口吻,以唯我独尊的姿态重新祭出“价值普遍性”的神坛,坚定地认为只有美国式保守主义价值才是人类文明的灯塔,甚至一言不合就会大打出手,对境内外所有持有异议的人士和社会进行粗暴干涉,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固执和偏执。显然,在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眼中,经济问题已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价值问题、制度问题和身份认同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随着社会转型的基础发生位移,美国早期“帕灵顿范式”强调的单一“美国心灵”已经今非昔比。美国政治的保守化趋势背后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只不过此种封闭不再是受制于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当年提到的价值相对主义,而是受制于自以为是的价值绝对主义。
(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虽然美国自身的变化是美国政治走向保守化的决定性因素,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也是影响美国政治保守化的重要外部条件。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美国世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美国自视为一个不同于旧大陆的“新世界”,是被上帝挑选的选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哲学是孤立主义,其专注于追求自由民主的事业,不卷入旧大陆的政治纷争,呈现出“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的悖论。面对自由竞争的国内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坚持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面对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坚持实力至上和霸权原则。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罗斯福推论”,贯穿始终的都是在国内实行自由主义,在国际上实行现实主义和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长期支配美国的孤立主义哲学,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美国开始实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全球主义哲学。无论是冷战期间服务于美苏冷战的“自由世界”,还是冷战后的“华盛顿共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都推动美国世界政治哲学发生变化,这一世界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就是以美国为模板,改造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一哲学主导了二战后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与之前的孤立主义哲学不同的是,美国人不仅在国内追求自由民主事业,也在国外推进自由民主大战略,尤其是冷战后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源自威尔逊主义的美国理想主义一下子弥漫着“历史终结论”的胜利喜悦,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传递着“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将全面统治人类社会的“福音”。
然而,源于冷战胜利和全球化浪潮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阻挡住美国国内社会变化引发的保守化趋势,新保守主义思潮借助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在21世纪初全面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最初,“9·11”事件引发了美国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危机、文明冲突和跨国犯罪等问题的忧虑。美国积重难返的移民问题、种族问题以及文化战争问题等与全球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给美国自鸣得意的冷战胜利心态以致命一击,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让美国瞬间产生了“历史又回来了”的焦虑,甚至开始思考所谓的“后美国世界”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美国方案的“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这一切都令原本自信满满的美国霸权重新陷入了困惑。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崛起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一系列重大变化,犹如一波波巨浪,不断地拍打着美国世界政治哲学的心理防线。原本在国内社会已经积蓄了强大能量的保守主义思潮在一连串外部挑战刺激下不断发展壮大,以独白式普遍主义的路线日益吸纳着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建制的思潮能量,不断巩固白人种族-民族主义基本价值观的思维框架,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哲学和国际政治哲学在保守主义的旗帜下走向合流,推动美国政治呈现出保守主义日益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潮景观。
结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变化是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整个世界越来越看不懂美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陷入恶斗的政治极化、积重难返的种族矛盾、退群断链的对外政策以及日甚一日的文化冲突,使原本引领世界的“优等生”反而成为麻烦不断的“问题生”。美国怎么了,世界怎么办?这是事关世界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
美国乱局的背后是美国政治生态的根本变化。所谓的政治极化只是一种错觉,是在理解美国时仅局限于美国政治小棋局表象而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如果将美国政治趋势放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棋局中理解,就会发现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走向保守化,而非走向极化。迄今为止,美国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势均力敌的格局,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在学界、政界和舆论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多数美国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是不同派别的保守主义信徒,这就是美国近年来反复强调所谓“新政治共识”的原因所在。
保守主义的全面升温,是美国国内小环境和当今世界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顺从了美国社会反思自由主义的要求,适应了美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新生态;另一方面,它也迎合了源于美国文化优越论与美国地位相对衰落产生的心理落差,迎合了美国上下的权力欲望和自大心态。对美国政治保守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和冷静的判断,在制定对美政策和处理对美关系时,要适应美国政治走向的变化,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皮肤管理进修 http://www.yanxikou.com/seniorclass